夏书章:治国理政之学,善政良治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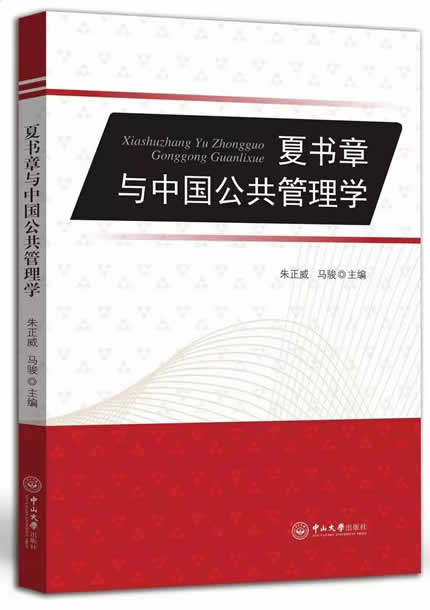
编者按:百岁夏老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他艰苦卓越的人生历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公共管理学一部活的学术史。夏老秉承“下医医人,上医医国"的人生志向,在充满曲折困苦的时代环境中恪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为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新的部署,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机遇和历史使命。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等话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热词。夏书章教授在评介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经典的同时,从治国理政的角度重新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中国意蕴。他用毕生的学术实践,展现了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建构的方法论原则和实践价值。作为他的弟子,西安交通大学朱正威教授以访谈的方式为我们近距离呈现了夏老卓越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展望。正如夏书章教授所著新书标题所言,“百年寻梦从头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出此稿,就是希望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及国家治理效能等重大议题,呈现来自公共管理学的初心、使命和学术担当。
摘 要:夏书章教授的百年求学和学术探索,不仅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历程,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与和他个人的治学史密不可分。他将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专业进行了中国化的定位,即行政之行,行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专业之专,专的是为人民服务,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是一门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社会公仆的专业。他指出,公共管理对于善政良治具有直接、密切而深刻的影响,70年的国家治理历程已经证明,高品质的公共管理知识供给,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共管理知识分子要秉承治国理政的远大抱负,为民族复兴贡献理论智慧。
关键词:公共管理;治国理政;学科发展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
的学术志向
01
求学经历
朱正威:您曾用“上医医国”来表明您的人生志向,可否向我们回顾一下您的求学经历?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将个人追求与民族命运相联系,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夏书章:任何人的成长成才,首先是个志气的问题。中国人的文字很有意思,志,就是士的内心,凡人都要有个志气,有个目标,不能稀里糊涂混饭吃,浪费生命。所以,看一个人要看两点:其一,有无志气?其二,有什么样的志气?正如我们现在倡导的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和使命,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最初所立的志向。人而无志,不知其可。三心二意、意乱神迷、见异思迁、胡思乱想等等,都不符合坚定志向的要求。我出生于旧社会的一个平常家庭,所处的时代环境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儿时对天下事、国家大事并无深刻认知。加之生活在江苏高邮县(现已改市)送驾桥(今送桥)镇,媒体和通讯都不发达,几乎未接触电视、报纸,对外部世界的信息知之甚少。但我却亲历了“过兵”事件,目睹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败兵过境祸害乡里的恶行。后来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外国侵略势力扶植不同的军阀,中国大地充满了战火硝烟。以致于这样的顺口溜得以流行:去年两个打一个,今年两个互相打,不打不得烂,打给外人看。国际上甚至已有“中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地理名词”的说法。所以准确地讲,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是国将不国,而是国已不国了。由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我的求学过程也遭遇了一些波折。初中学习两年后,家里再无力支持我求学,到南京之后我又遭遇了失业,进退两难之际考上了高中。期间,在师友帮助下,有幸被减免了学费,还获得了在民众夜校兼职的机会。后来,经历了第一次到上海考大学、到重庆读大学、到哈佛大学念公共管理、回国任教等等,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从江苏徐州转往广州的中山大学。这些经历拓展了我的眼界和思路,促使我对人生的道路做出选择。身处这样的历史环境,我从小十分欣赏“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观点。当时想的不是什么前途、工资、将来担任什么职务,想的是国家和社会怎么样变革、提升。我觉得国家“患了病”需要医治,最好的医生是要把国家“医治”好。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兴旺,就需要医治国家的医生。所以,我们个人的前途,必须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是我们作为个人的奋斗初心,也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志向。
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有人会难以理解,我既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受的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教育,为什么会追寻中国共产党?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我出生在五四前夕,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民生凋敝,被称为“东方的睡狮”“东亚病夫”。为了解决军阀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以国共合作为主的进步力量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可后来国民党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道路,加重了国难。9·18事变中,日本人莫名其妙就把东三省拿掉了,一个日本就打败了我们泱泱中华。因为一穷二白、积贫积弱,谁都欺负我们。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老百姓都很着急,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致抗日。1937年后,国共联合抗战,但实际上国民党还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亲历这些历史事件促使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些现象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当时已经明确感知到国共两支军队确实存在差异,应有所取舍。民主人士一到延安,就作出了鲜明对比,新中国的建立,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我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必定胜利的发展趋势和结果,这为我希望终身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打下了思想感情的坚实基础。所以,我在1956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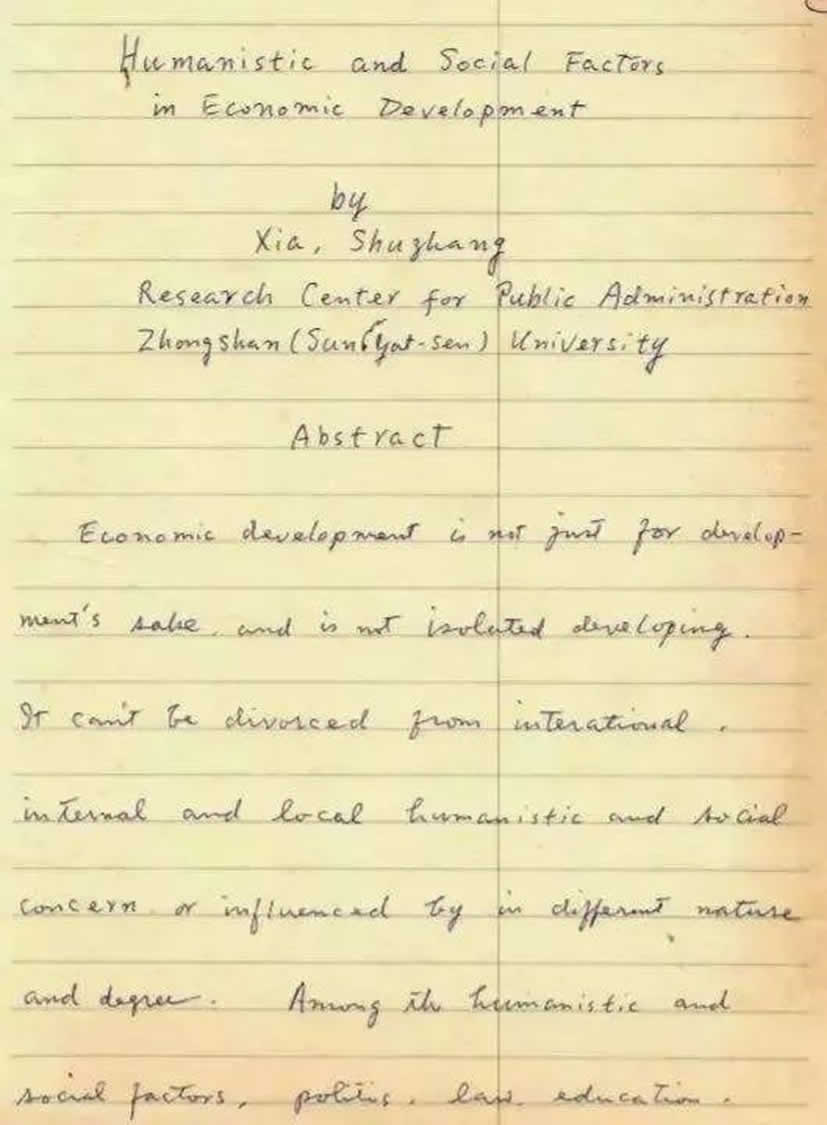
朱正威:秉承这样的志向,您一直从事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学界将您评价为中国公共管理学活的教科书。而您在抗战期间的求学阶段就确立了政治学这个终身学习和研究的领域。从专业选择的角度,您其实面临非常丰富的选项,理工、经济等热门专业一直很受学生追捧,而您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矢志不渝的研究领域。可否和我们讲述一下当时做出这种选择的考虑?
夏书章:我为什么选择政治学?为什么要一直从事行政管理或者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我中学时,各科成绩都不错,而当时,最时髦的是理工科,尤其是工科,人文社科里面是经济学最热门。我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我自作主张,选择了政治学。最简单也可以说是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强大,想通过对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明白国家强大的机理,找到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方案。政治的治,顾名思义,就是治理。行政学,就是现在的公共管理学,其根本的使命也是研究这个治理之道。公共(行政)管理这个学科是引进的,英文叫publica administration。一开始,日语和中文,都翻译成行政,是因为它是从政府开始的,后来有了公共管理的说法。广义的行政学,也包括非政府研究,公共管理的外延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涉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国家能否兴旺发达,最本质的就是要看治理水平!经济不解决问题,必须要通过政治来救国。当时就是怀着这种“天真”的心态,“自作主张”坚持读了政治学专业。同时我也深信,只有建立和健全文官制度,才可以解决吏治腐败问题,所以就选择了行政学的研究道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我们今天说的“中国梦”,其实也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