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跨学科系列】刘华杰:马丁·路德之后500年:人类可持续生存与重启博物之学
2023年12月5日下午,由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联合推出的“科学与人文”跨学科系列讲座第五讲在中山大学南校园学人文库如期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刘华杰教授主讲“马丁·路德之后500年:人类可持续生存与重启博物之学”,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院长庞虹教授主持。
一、千年尺度下的“中介”问题:从马丁·路德讲起
学问有径,方法先行。刘华杰教授首先介绍他所采取的方法论——“变焦”。这与朱良志教授提出的“乾坤透视”异曲同工,都强调将事件置于历史长河中,以伸缩变换的时间尺度去多维丈量。本次讲座的题目“马丁·路德之后的500年”,将16世纪的宗教改革置于千年尺度下观察,就是“变焦”方法论应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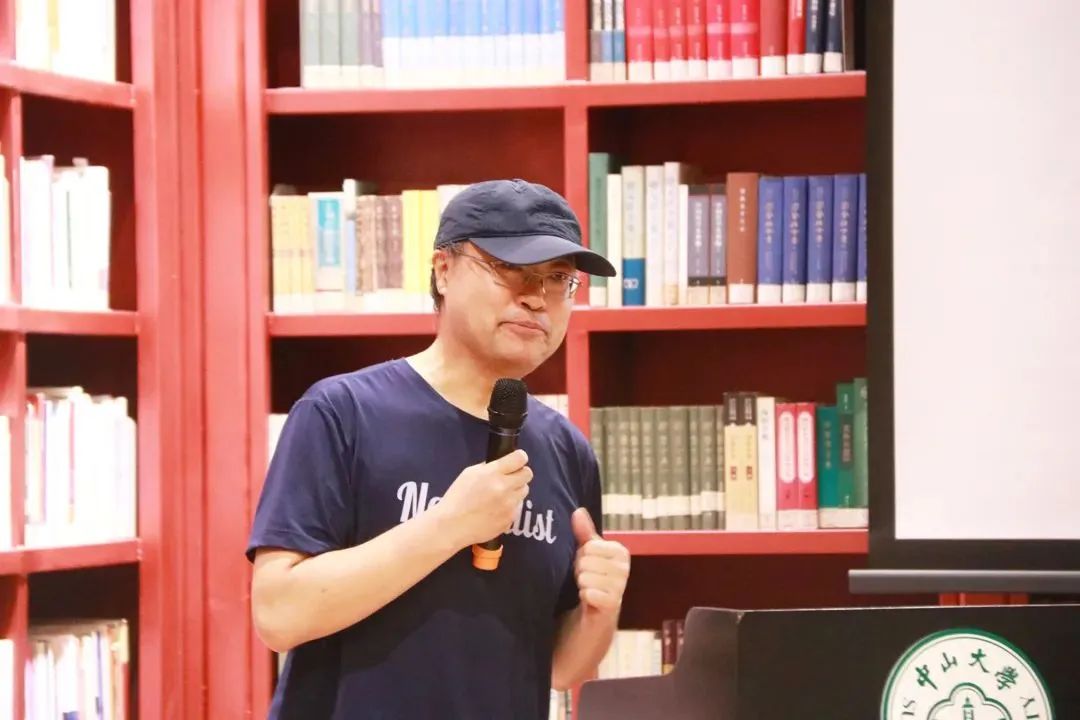
刘华杰教授进一步指出,本次讲座重点探讨的是“中介”问题。受限于认知水平,人和自然的对话需要“中介”帮助。从文艺复兴到信息革命,人类历史上的每次重要变革都伴随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人和自然之间的“中介”也在不断演变。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下,我们看到,曾经掌握话语权的基督教文化已经让位于自然科学,科技成为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中介”。
之所以选择从马丁·路德讲起,是基于刘华杰教授的观点:当时宗教改革的影响远超科学革命。哥白尼的科学革命局限于精英阶层,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却具有民族性和大众性,全方位解放了普通民众的思想。从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宗教改革为巩固宗教地位而生,却最终引向了宗教地位的下降。
刘华杰教授详细介绍了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基本情况和改革进程。1517年,时任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师的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公开质疑罗马教皇和教会在宗教中的中介作用。刘华杰教授强调,路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否定属于“内在否定”,因而更加有力。随后,路德致信教皇,斥责其代理行为的僭越性,并冠之以“敌基督者”的罪名。1520年,遭罗马教廷教谕警告后,路德转向激进,连作三篇檄文《论德国基督徒的尊严》《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徒的自由》以声讨教会。
其中,刘华杰教授着重介绍了路德关于“圣餐”的观点创新:他主张将圣餐饼酒平均分给每一个愿意领受的人。紧盯真正的圣餐知识,用质朴实在的语言加以论述,体现了路德恢复常识、回归大地、回到生命出发点的努力——毕竟温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最基本的环节。
宗教改革的核心观点“因信称义”,即只要真心实意信仰上帝,灵魂便可以称义、可以得到拯救。信仰本身就是充分必要条件,与“事工”多寡无关。这一观点的主要用意是弱化中介,防止中介的擅权和滥权。在路德的解释中,《圣经》分为“诫命”和“应许”两部分,唯独上帝可以制定和成全“诫命”,这部分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而信基督可以泽被恩典,万事都被“应许”了,这部分让信徒得到自由。
路德的学说看似简单但意义巨大:它重新框定了人与上帝的关系。普通人有权利和能力直接认识真理、认识上帝。思想解放后的西方人放下包袱,从此轻装前行。同时,由于集体生活、集体意志被削弱,个人主义抬头,极大激发了科学的原创性。刘华杰教授列举默顿命题和韦伯命题,阐明基督教、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长期来看对西方科学发展都有很大程度上的促进作用。马丁·路德之后500年,完全出乎他的个人意愿,上帝悄然退位给自然,科技取代教会成为了新的“中介”。
二、科技创新神话:对反思与批判的呼唤
500年后,科技日新月异,芯片、无人机、AI等技术层出不穷,生活提速带来普遍焦虑,人与自然疏离。现代科技面临新的异化问题:作为大自然与平民百姓之间的中介,科技的权威实际超过了当年的教会;高科技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当下需要和环境承载的能力;科技在集成人的智力的同时也化身武器和帮凶;风险社会中,科技成为最大风险的来源,它威胁着“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角色宣之于口:满足欲望的权利已经平等赋予了每个人,但满足欲望的方法尚未指明。科技创新似乎提供了办法,但也导致了“仇富劫杀”。在科学里,陀氏没有看到科学精神,只看到“the object of sense”。同样,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对丽莎说“只要我能得到安宁,我立马会把整体世界以一个铜子贱卖!”这句话展现了极端形式的个体主义。正是这种个体主义支撑了科技创新,但同时也揭示了一种扭曲的世界图景。
科技创新业已成为新的神话和教条。它有两个基本预设,一是进步性假定,即科技创新必然代表着进步;二是单调性假定,即科技创新可以打压竞争对手,对己方全员有益,并能最终提高人类整体生存能力。传统社会奉行的是达尔文式创新,突变率低,系统稳定;而现代社会则推行新式的所谓弗兰肯斯坦式创新,系统不稳定,自毁概率增大。
理性的人类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例如全球军费支出高达约两万亿美元,军备竞赛浪费惊人。虽然四次大的科技革命在短期内带来了正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却隐患颇深。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革人的命”,否定人类肉身性的存在,完成从A(原子atom)到B(比特 bit)的飞跃。从演化论的角度看,竞争和创新也只是二分法的一个方面,脱离另一面就有危险。科技创新神话的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首先,它加剧了社会集团、子系统之间的恶性竞争;其次,它行为绑架,加速生活节奏来让游戏者疲于奔命;最后是智力反噬,我们学习大量的知识、发展高科技武器以打击敌人,但最终这些知识可能会反过来伤害自己。
刘华杰教授提到了当代技科(technoscience)的浮士德形象。浮士德的特点是理性、不断进取和求知,但永远推卸责任和拒绝反思。他不在乎真善美的价值。魔鬼梅菲斯特一开始就是浮士德身上的一部分,他不仅是工具,也承担了道德责任。如今的科学同样在日新月异的同时推卸责任,运用哈姆莱特式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自我辩护。今天的科学很多时候只是经过包装的“轻率”,而“轻率”会招致“毁灭”。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资本、权力三者形成了一种铁三角关系。在前两者被广泛批判的同时,对科技的反思却是缺席的。对于这种不平衡现象,科学哲学界的另类人费耶阿本德提出:“即使你并非一名科学家,也能批判科学的贪求。”科学的民主批判不仅不荒谬,而且属于知识的本性。人文学者必须承担反思与批判的责任,反对过度的、撕裂的创新。
刘华杰教授指出,科技伦理已经不管用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人文批判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劣势,为了扭转这种劣势,刘华杰教授呼吁重启博物之学以反思科技之墙,开启物质实践。
三、重启博物之学:人类可持续生存的一种可能
“重启博物之学”的设想,出于刘华杰教授个人对科学哲学、现象学、科学编史学、文明史的广泛涉猎和综合考虑。他相信,经过历史检验的古老博物学,会在今天焕发全新的生机。
要重启博物之学,必须反思中介的作用。刘华杰教授指出,科技中介对于人类个体造成了多重影响。首先掌握一定科技知识的人傲慢大意,其次普通人探究大自然的愿望降低甚至表现出胆怯与懈怠,最后,知识迅速增长并绑架所有个体,使之成为人造机器的尘埃。
博物首先是对现代性匆忙的一种克服,它重申圣雄甘地的观点,认同“二分法中的慢也是一种价值”。其次,博物学注重个人致知的环节,即将公共知识消化理解吸收成为个人知识的过程。在明确这两点的基础上,刘华杰教授提出了建构我们的博物(BOWU)之学,他将四个字母扩充为四个单词,以诠释他对博物学的理解:
“Beauty” 天地有大美不言
“Observation” 观察、记录、分类、探究
“Wonder” 童心和惊奇感
“Understanding” 寻找理解、可持续共生
刘华杰教授强调,关键在于转变我们的观念。科技并不等于正确,我们应该充分考虑风险、严肃科技政策的制订,弱化但并不取消中介的作用,努力用现有科技知识武装个人头脑,然后在自己学识范围内针对性支持有利于可持续生存的科技研发。
路德改革时有口号“因信称义”,因信仰获得正当性,而今天的博物复兴也有口号“自然行道”,坚持自然本性,以获得合理性。我们必须反思,科学定律一定反映自然意志吗?科学世界一定高于生活世界吗?科学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解决吗?针对这些反思,刘华杰教授提出博物之学,要点在于,博物之学是自然之学,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策略一致,与环境兼容。
新博物学的核心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限定性地传承古老博物之学(natural history)。第二,反思唯科学主义,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努力使个体访问大自然的非科学通道保持开放。第三,主张平行论,认为博物学过去、现在和将来平行于自然科学存在和演化。第四,以自然主义为主,采取时空变焦方法,由近及远认知万物。重视地方性知识,全方位探究自己的家乡。第五,奉行生态价值观,为了行稳致远,倡导博物伦理,主体合作与天人协同。
刘华杰教授随后介绍了自己撰写与翻译的若干著作。他强调,探究大自然同样是人文社会研究者的使命,且此权利不可随便让渡。最后他用三句中国古语概括了博物的三层面: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物物而不物于物,自然以自由。颇具中世纪装潢风格的五彩琉璃窗见证了这一场跨越五百年、横贯中西方的回首与展望,在忧患与振奋两种情绪的交织中,讲座步入尾声,但听众的思考绵延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