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武:要多备几副笔墨
“老一辈人文学者造诣高深,治学无此疆彼界,多学科贯通,往往能收左右逢源,融洽圆足之效。前辈教导我们说,要多备几副笔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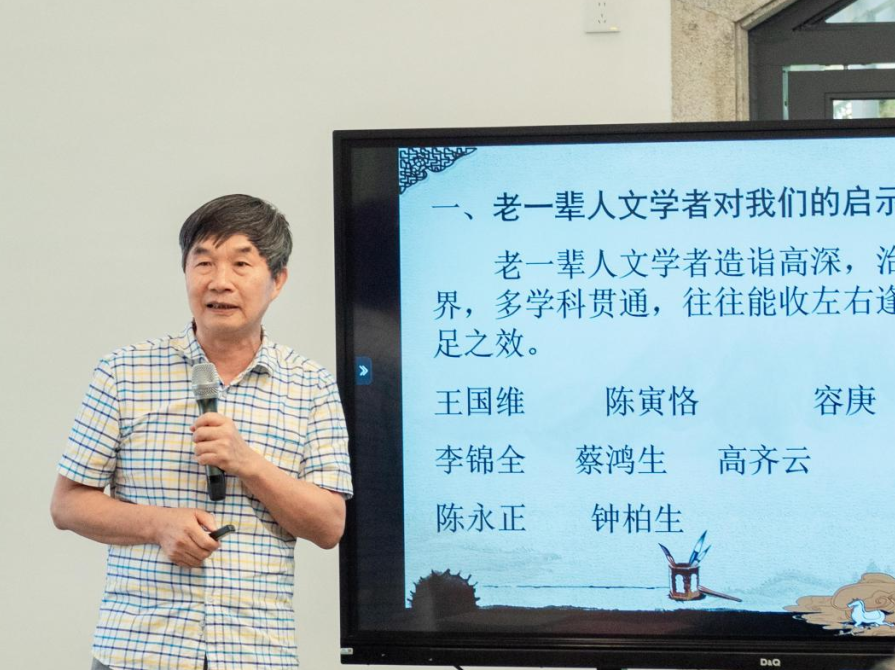
学术工作坊上发言
要多备几副笔墨
——浅谈人文科学多学科的交叉为用
文|陈伟武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时代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不过,老一辈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各有各的贡献,各有各的精彩,他们的卓越成就和宝贵经验,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古代学科畛域不严,学者往往文理医工兼通。汉代天文学家张衡也是文学家。明代方以智、清代顾炎武、程瑶田、钱大昕等等,无不精于天文、地理、历算之学。现代学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饶宗颐等前辈都学贯中西,成就多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东渐给中国传统学术传统及学术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学科越分越细,画地为牢,株守一科,坐井观天的治学模式,流弊甚广,积重难返。
如何打破学科藩篱,振衰起弊,继承优良学术传统,大有可为。就我自己稍为熟悉的一些中山大学学者而言,容庚、邱世友、李锦全、蔡鸿生、高齐云、陈永正等教授,都是在文、史、哲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可以师法的典范。
容庚先生的学术领域主要在古文字学,《金文编》和《商周彝器通考》都是现代学术史上熠熠发光的经典之作。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和艺术史研究领域,容先生同样多所建树,如早年容先生深入研究过《红楼梦》,曾就版本问题撰写长文与胡适先生商榷。与詹安泰、吴重翰等先生合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负责上古文学部分的撰写。1950年底还在《岭南学报》上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论文《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

邱世友先生是著名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家、词学家,在文、史、哲三个学科的顶级刊物《文学遗产》《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都发表过学术论文。
李锦全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著作等身,有十卷本《李锦全文集》行世,却是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而且旧体诗词创作也成就颇高。
蔡鸿生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荦,著作有《蔡鸿生史学文编》《读史求识录》《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等等。蔡先生古典文学造诣湛深,擅长以诗证史,深得陈寅恪先生治学神髓。每做一个题目,上天入地,穷搜博讨,如抽丝剥茧,论证周延密致,结论往往振聋发聩,一新耳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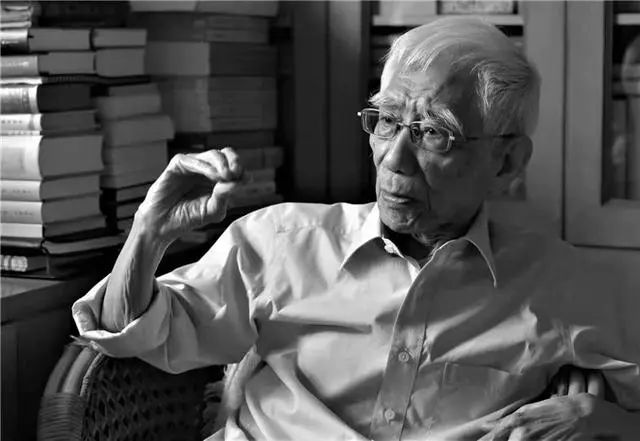
高齐云先生毕业于中大中文系,深入研究李白诗歌艺术成就,尝有长篇论文发表。后在哲学系工作,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高齐云自选集》等著作。
陈永正先生从容庚和商承祚两位教授习古文字学,研究领域为汉语言文字学,在春秋金文联结词等专题有专精的研究,但其主要成就却是在中国古代诗词文献学和岭南文献的全面整理和研究,有《诗注要义》和《全粤诗》(主编)等著作。陈先生是一位融贯文、史、哲,兼通儒、释、道的通才式学者。
老一辈人文学者造诣高深,治学无此疆彼界,多学科贯通,往往能收左右逢源,融洽圆足之效。前辈教导我们说,要多备几副笔墨。可惜现在专精某一研究方向的“专家”多,兼通多个学科的“通才”少,著述行文,稍为溢出自己熟悉的学术领域,很容易就会说外行话,容易出现硬伤。学科之“隔”非常严重。“不要捞过界”的警示语时常在我们耳边响起,这是师长辈提醒我们后学对其他学术领域要有敬畏之心,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会成为我们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遁词,也会成为消极因素影响我们拓展学术领域的动力和潜能。
我自认不学无术,浅薄谫陋,实在不足以议论学问的博与专,只可作为反面教材为来学者提供一些借鉴和教训。
我小学和中学阶段刚好是“文革”十年,没读到什么书。1977年高中毕业后流浪了两年,1979年侥幸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可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大一大二那两年,我通过黄光武先生的引荐,由陈焕良先生为我开列了一些语言文字学的入门书,如饥似渴地学习。不过,由于自己愚钝,读书不得法,浪费了不少时间精力,走了弯路。大三时,我自拟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古汉语词义转移界说及其类型》,由李星桥(新魁)先生指导,可算略窥语言学研究的门径。1983年大学毕业,考上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潘弢庵(允中)师习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1986年硕士毕业留校,在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工作。1991考上曾经法(宪通)师的研究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慢慢地走上了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之路。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读书时,小学只有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至高中毕业,总共才读了九年书。我自小学四五年级和中学阶段,因小姑父陈岳彪先生是上社大队民兵营营长,长期得以阅读民兵营的《解放军报》,又在每天放学后都会跑到老人组(即大队办的敬老院)里读《人民日报》,这样的阅读生活对我后来的学习应该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自己选了做兵学的题目,曾师表示支持并精心指导,1999年以《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为题由中山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简帛兵学文献涉及面甚广,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考察属于我的本行,同时要从若干其他侧面加以讨论,如要考察简帛兵学文献的内容和性质、评价兵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读了不少诸子的书,才能对兵家与儒、道、墨、法、阴阳诸家的关系略加评骘。要讨论简帛兵学文献的文化内涵,我从军礼、军法、军术三方面入手阐述。其中一节内容为《简帛所见军法辑证》,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后来收入杨一凡、刘笃才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乙编第一卷《法史考证重要论文选编﹒律令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古文字学的学科性质,说得不好听就是边缘学科,说好听点就是交叉学科,牵涉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等多种学科。自己写过一些内容有点芜杂的论文,例如:《简帛医药文献考释举隅》《战国楚简所见病名辑证》《秦汉简帛所见病名辑证》(以上三文与张光裕先生合作)《简帛医药文献所见地名及药物产地浅说》《简帛文献中的医药禁忌》《从简帛文献看古代生态意识》《简帛文献中的残疾人史料及其相关问题》《试论简帛文献中的格言资料》《出土战国秦汉文献中的吉祥语》《简帛占验术文的产生与字词形音义》《古代称谓行辈失序证例》《骂詈行为与汉语詈词探论》等等,都是自己遵照李星桥教授的教导,利用做题目来读书,拓宽学术视野的有益尝试。
我所从事的只是很小众的学问,做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也做一点汉语史研究,几十年来庸碌无为,乏善可陈。从自己个人极其有限的认知里,我体会到了文、史、哲一家亲的学理,也深切明白中文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开展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前人说知人论世。要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当然离不开要考察那个时代的文学所由产生的背景,包括思想思潮、时空条件。研究某一时代的语言文字,何尝不是如此,都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对待语言文字的传承和演变。
因此,要研究中国语言文学,都有必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地开展交叉研究,才能全面而真切地探求中国语言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静止的、单一的、片断的研究方法都难免如盲人摸象,落于一偏,或抱残守缺,削足适履。我们如今身处大数据的时代,琳琅满目的电子书、电子数据库和无远弗届的高科技检索手段,都为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大开方便之门。数字人文研究前程无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辉煌成就,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本文为陈伟武教授据2023年6月26日“跨学科:观点、案例与经验”工作坊发言稿增订,正标题为编者所拟)


